主角忍冬陈望出自小说推荐《路边男的不要捡》,作者“苍苍草露”大大的一部完结作品,纯净无弹窗版本非常适合追更,主要讲述的是:【乱世\/强取豪夺\/微虐\/逃荒\/哑女\/偏写实\/无玛丽苏\/中短篇】都说路边的野男人不要捡,轻则骗你心,重则要你命。但我已经捡回来了……等等,他好像还不错?捡的第一个男人,要娶我。他教我写名字,红着耳朵说:“岁岁年年,我们有一辈子慢慢来”。后来我才知道——路边的野男人真的不能乱捡。捡的第二个男人,自称落难商人,伤得楚楚可怜。可他伤好后摇身一变,成了顶级门阀贵公子。他替我翻案,语气轻飘飘:“顺手而已。”他邀我入府,眼神沉甸甸:“许你为妾。”后来,他当着我的面,将弩箭送进了第一个男人的心口。他将我锁入金笼,“你一个哑女,除了跟我,还能有什么出路?”我指向心口。我的出路,不在后院,在四方。哪怕前路是饿殍遍野,是刀兵加身,我也要用这双脚,走出一个人的模样。这世道吃人。但我要活。一寸一寸地活。⚠️重要提示:1.女主身残,社会最底层,时代局限性非大女主,第一人称女主视角,沉浸式乱世漂流。2.架空历史呈现乱世流民生态,剧情残酷贴合时代背景(如流民困境、强权压迫),后续可能更压抑,不适请即刻退出。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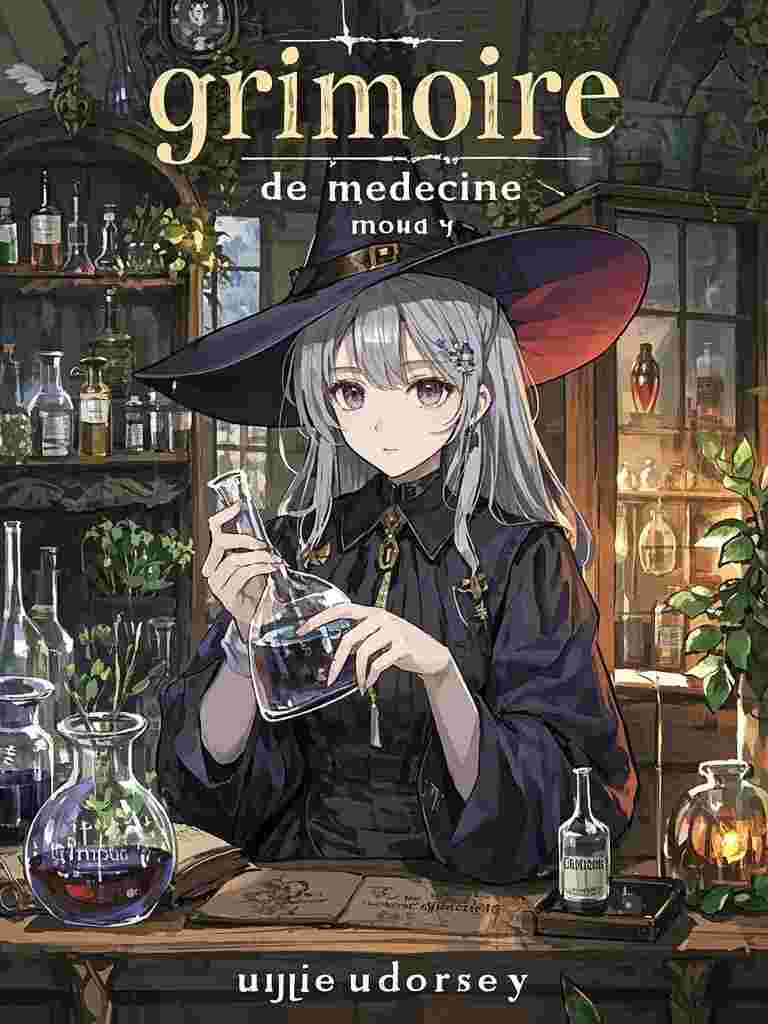
小说推荐《路边男的不要捡》,是小编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推荐,代表人物分别是忍冬陈望,作者“苍苍草露”精心编著的一部言情作品,作品无广告版简介:“咱们先去找个大户人家的庄园或者坞堡,卖力气干活,攒点路费,也打听打听门路。活人还能让尿憋死?”见我不说话,她默了一会儿,那双亮得过分的眼睛盯着我,声音压低了些,却更沉:“你虽然不吭声,但我瞧得出来,你心里憋着一股气,一股子狠气,是恨吧?恨那些糟践了你、害了你亲人的人?”我猛地一颤,手指下意识收紧,...
阅读最新章节
她的话很简单,却像一块小小的火石,在我心底擦出了一点微弱的火星。我慢慢把饼子放进嘴里,用力咀嚼,这是逃亡以来,尝到的第一口有滋味的东西。
小禾很自然地挨着我坐下,“我看你一个人,也没个伴儿。我要北上,去冀州那边寻亲。我有个远房表兄,在清河崔氏府里做事,听说伺候的是一位公子。那可是了不得的人家!你……要不要跟我一道?路上有个照应,总比一个人等死强。”
我抬头看她,眼里是死水般的茫然。
她拍了拍我的肩膀,力道不小,拍得我身子一歪。“咱们先去找个大户人家的庄园或者坞堡,卖力气干活,攒点路费,也打听打听门路。活人还能让尿憋死?”
见我不说话,她默了一会儿,那双亮得过分的眼睛盯着我,声音压低了些,却更沉:“你虽然不吭声,但我瞧得出来,你心里憋着一股气,一股子狠气,是恨吧?恨那些糟践了你、害了你亲人的人?”
我猛地一颤,手指下意识收紧,指甲掐进掌心。
她顿了顿,“我爹妈死得早,嫁了个男人,没两年家乡闹兵灾,男人没了,婆家嫌我克夫,把我扫地出门……啥腌臜气没受过?啥白眼没看过?不也还喘着气,没让阎王收走么?”
她语气平淡,像在说别人的事,可眼睛里瞬间掠过的痛楚,我却看得分明。
我心里一紧,抬眼看她。
她一把抓住我冰凉的手,她的手心粗糙,布满茧子和细小的伤口,却滚烫。“所以!妹子,恨,就记着!但光恨顶屁用?你得先活着!活得比那些王八蛋长,活得比他们硬朗,才有机会把这口恶气吐他们脸上!听姐的,咱先想法子把命保住,把身子骨养结实点,再说别的!”
活着。先活着。
这两个字,从小禾嘴里说出来,不是沈医娘那种沉甸甸的嘱托,不是柳婶儿那种含泪的哀求,不是余音那种空洞的诀别,她的眼里只有一种近乎蛮横的、对“活下去”这件事本身的执着。
我反手,用尽此刻能凝聚的全部力气,紧紧抓住了她滚烫的手,用力点了点头。
小禾就像一道横冲直撞的光,硬生生劈进了我一片死寂的世界。她带着我,混进一股更大的、往北迁徙的流民队伍。
路上,她教我辨认更多能吃的野菜野果,哪怕是最苦最涩的,她也能说出哪部分毒性小些。
“喏,这个马齿苋,掐嫩头,用水焯一下,虽然还是难吃,但吃不死人。”
“那个灰灰菜的根,埋火堆里煨熟了,勉强能顶饿。”
夜里寒风刺骨,我们就挤在破庙墙角、草堆里,紧紧挨着,互相取暖。她话多,会讲她家乡河沟里摸鱼的事,讲她见过的稀奇古怪的人,也会低声咒骂世道,骂那些刮地皮的贪官,骂那些杀千刀的乱兵。
跟着流民大潮,不知走了多久,终于看到远处地平线上矗立起一道灰黄色的高墙,墙头有箭楼,那就是坞堡,本地豪强聚集宗族、部曲自保的土围子。堡外依附的流民窝棚密密麻麻,像一片巨大的的烂疮。
小禾拉着我,挤过臭气熏天的窝棚区,直奔坞堡侧门。那里有几个管事模样的人,正挑拣着流民里还算看得过眼的青壮。
“两位爷!行行好!收下我们吧!我们能干活!什么都能干!”
小禾挤到最前面,声音又亮又脆,脸上堆着笑,却把腰板挺得直直的,“我力气大,能舂米,能挑水,能喂牲口!我这妹子,”她一把将我拽到身前,“手巧,听话,能缝补,能打扫,吃得还少!”
那管事斜睨着我们,又捏了捏小禾结实的胳膊,从鼻子里哼了一声:“进去吧。西边最破那排窝棚,找刘婆子领活儿。丑话说前头,偷懒耍滑,立马滚蛋!死了残了,自己找地方埋,堡里不管!”
我们总算有了个能挡雨的窝棚,每天天不亮就起,阿禾被分去舂米。那石臼又大又沉,木杵抡起来,砸下去,发出沉闷的咚咚声,从早响到晚。她很快成了那一组最能干的,别人一天舂三斗米累得胳膊都抬不起,她能舂四斗半,汗水把粗麻短褐浸透,贴在身上,勾勒出结实有力的线条。监工的婆子都对她另眼相看,有时会多给她半勺稠粥。
我被分去浆洗和缝补。成堆的、散发着汗臭的衣物,在冰冷的河水里泡,用木棒捶打,手很快就冻得通红,又肿又痒。晚上,就着豆大一点的油灯缝补那些磨破的衣裳,针脚必须细密,否则要挨骂。
吃的是粗糙的麦粒混着麸皮,有时还掺着没筛干净的沙土和稗子,硬得硌牙,得就着稀薄的、只有几片烂菜叶的豆叶汤才能咽下去。
阿禾因为能干,有时能多得半勺饭或一小撮盐。她总是偷偷分我。
“吃!看你瘦得跟麻杆似的,风一吹就倒!多吃点,长点力气!”她不由分说,把稠的拨到我碗里。
我额前的刘海始终厚重,那道假疤成了我的护身符,让我在这混乱的地方少了很多麻烦。"
